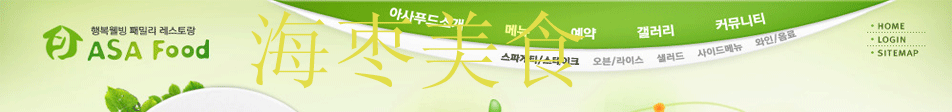|
司马迁的故里究竟在哪里?也就是司马迁的出生地即他的籍贯究竟在哪里?对于这个问题,司马迁死后的二千多年里,一直有争议。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是绛州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,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是冯翊夏阳(今陕西韩城)人。元代,司马迁是河津人尚无争议,明代后期至清代,争议明朗化。新中国成立后,不少资深专家学者经过分析研究,都认为司马迁出生在河津,是河津人,河津是司马迁故里,应当理直气壮地载入河津史册。 1、司马迁自报家门说:“迁生龙门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明确表述: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”。这里所说的“龙门”,即大禹治水时所凿的龙门,也叫禹门口。“河”即黄河,“山”即龙门山。按照地理方位规定,河之北曰阳,河之南曰阴,山之南曰阳,山之北曰阴。司马迁所说的“河山之阳”,即黄河以北,龙门山以南,从地理位置看,河津正处于这个坐标中心。当时,河津称皮氏县,这里北枕龙门山,西囊禹门口,南与西均毗邻黄河,依山傍水,正位于“河山之阳”,确实是一块蟠龙卧虎的宝地,司马迁正是以大禹治水所凿的龙门大好河山,来抒发自己对家乡所处地理环境的自豪。可以说,“龙门”即是皮氏县的代称,正因为如此,北魏即改皮氏县为龙门县,宋代始改为河津县,而河津至今仍称“古耿龙门”。正是在这样有着美好传说的家乡,少小时的司马迁曾经在龙门山下的黄河岸畔放牧牛羊,帮助家人耕田,这种热爱家乡的自豪感,由司马迁自己亲笔记录于个人的“履历表”——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,这是认定“司马迁是河津人”的最有说服力的第一手材料和历史证据。 《史记》问世后,南朝宋裴骃为之注释,曰《集解》,唐代司马贞为之注释,曰《索隐》,唐代张守节为之注释,曰《正义》,宋代将这三家注释分别排入正文之下,便于阅读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“迁生龙门”一句下,有这样的注释:“《正义》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,其山更黄河,夏禹所凿者也,龙门山在夏阳县,迁即汉夏阳县人也,至唐改曰韩城县。”上述解释认为龙门是指大禹所凿的龙门,但龙门山在哪里,《正义》的解释是错误的。年出版的《辞海》对“河津”的注释说:“黄河禹门口(龙门)在县境西北。古迹有司马迁故里。”对“龙门山”是这样注释的:“龙门山在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及陕西省韩城县东北,跨黄河两岸。悬崖壁立,巨涛奔流。上有禹王庙。”汉代孔安国的《尚书传》说:“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”,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说:“龙门山在河东皮氏县西”,唐代颜师古说:“龙门山在龙门县北”,从古到今,龙门山、禹门口、龙门,都记载在山西省河津县。就以《辞海》的解释而言,龙门山也不单在韩城县,唐代张守节在《正义》中所作的“龙门山在夏阳县”的解释显然是片面的,是错误的,由于前提错误,因而得出错误结论。这一错误结论,恐怕是千百年来说“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”的重要依据,很可惜,这是个错误的依据。 2、晋朝汉阳太守殷济为司马迁墓建石室,立碑树垣。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在《河津县总图记》(载明万历版《河津县志》)中明确记述:“司马迁墓前有庙,庙前有碑,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,立碑树垣。”这说明河津在晋代就有司马迁墓和庙。晋怀帝永嘉四年(),汉阳太守殷济奏请皇帝为河津的司马迁墓建石室,立碑树垣。或许是因为晋朝皇帝与司马迁同姓,或许是因为司马迁著《史记》的影响,殷济的奏章很快得到晋怀帝的批准,于是,殷济来到河津,为司马迁墓建了石室,并立碑树垣以资纪念。这些纪念物也比现今韩城的太史祠墓早七百多年。为什么晋朝要在河津而不在韩城为司马迁墓建石室、立碑树垣?很明显,就是因为当时河津有司马迁墓,而韩城没有,足见司马迁在晋朝时就被官方和社会列入河津籍。 3、唐代诗人牟融曾作《司马迁墓》诗。司马迁生于何时、死于何时、死于何地、葬于何地,都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历史学家推算,司马迁大约生于公元前年或前年,卒于公元前87年前后,享年58岁左右或“花甲初度”。他的《史记》大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(公元前-前91年)撰成,撰成后,他将底稿交给女儿和外孙杨恽保管,此后,他的事迹再不可考。汉宣帝在位时(公元前74年-前49年),外孙平通侯杨恽,“祖述其书,遂宣布焉”,《史记》才得以公诸于世。司马迁死后的三百多年间,由于《史记》的宝贵价值,司马迁的事迹才得以在全社会广为传播,于是,才有了他的墓地,而后又有了他的祭祠。唐代诗人牟融写过一首律诗,题为“司马迁墓”,说明他到司马迁墓前瞻仰过。他在诗中慨叹:“一代高风留异国,百年遗迹剩残碑。经过词客空惆怅,落日寒烟赋黍离。”意思是说,司马迁墓由于战乱破坏只剩下断碑残垣。瞻仰司马迁墓的过客见此荒凉景象,无限悲伤,吊古伤今,徘徊不忍离去,乃作《黍离》诗而抒发感伤之情。牟融的这首诗收录在《全唐诗》第卷,以后又收录在明万历元年()创修的《河津县志》卷十三“艺文”篇,说明唐代河津就有司马迁墓。古《河津县志》明确记载:“汉太史公祠在县西”,“汉太史公墓在县西”,“司马迁墓前有庙,庙前有碑。”这里所记述的司马迁墓,很可能就是牟融当年瞻仰过的司马迁墓。可见,司马迁死后,要么“叶落归根”,葬于故乡河津,要么,由其后裔在故乡河津立墓建祠,不然,牟融是写不出《司马迁墓》这首纪念诗的。 4、“司马迁是河津人”——元碑佐证。年2月24日,任罗乐、张瑞珍等专程到河津固镇村邵家岭寻访有关司马迁的传说古碑。上午十时,乡里赵先生帮他们掘出窑洞旁水龙头基座中的石碑,他们如获至宝,立即洗碑索迹。尽管这通元代石碑已经一分为二,且有数行字迹损毁,但有关“司马迁”的文字,仍然清晰可鉴。 该碑为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,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(7),碑文题为“创修上生院记”,由元朝从五品官员“奉训大夫陕西奉元路(西安)府判段循撰”文。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”,试摘录、标点,即为:“河津,古龙门县,大禹疏凿经之地,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,往往间出。”整句意思十分明确:河津古称龙门县,是大禹当年治水疏河凿山经过之地,这里曾经涌出司马迁等大文豪、大手笔,而且交替迭出,层出不穷。这段记载,为“司马迁是河津人”提供了确凿的碑证。这一元代碑文是河津市目前已发掘的碑文中,关于司马迁的最早记载。值得一提的是,碑文作者系陕西西安府判,他认为司马迁是河津的“弘文巨笔者”,与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所写《河津县总图记》关于司马迁的表述相一致。可见,在元代,司马迁是河津人,就已经成为官方与社会的共识。 5、明嘉靖十四年()《龙门志·人物》载:“汉太师史令司马谈,论家要旨(其详出《汉书》)。刘向、扬雄称其有良史才。太史令司马迁,十岁能文,太初中为太史令。修《史记》,传于世。向、雄亦称其有良史才。”这本尚存的明代河津县志,与元代《河津县总图记》一脉相承,都如实记录了“司马迁是河津人”的历史。 (作者系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会长、市人大原副主任) |